忠于自我带来的高生产力
原文:Productivity through self-loyalty
2014 年 11 月 2 日
1
只要我下定决心,工作效率可以高得惊人。
大多数人的心智模型基本按如下方式运行:我们嘴上说的「想要」只是试图控制大脑的无数声音中的一个,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使这些「群氓」的声音统一,去完成某些事情。很多时候,我们明明想停止拖延,却又无助地看着自己继续沉迷网络;或是明明下定决心迎接挑战,身体却像被钉在原地,只能看着机会从眼前溜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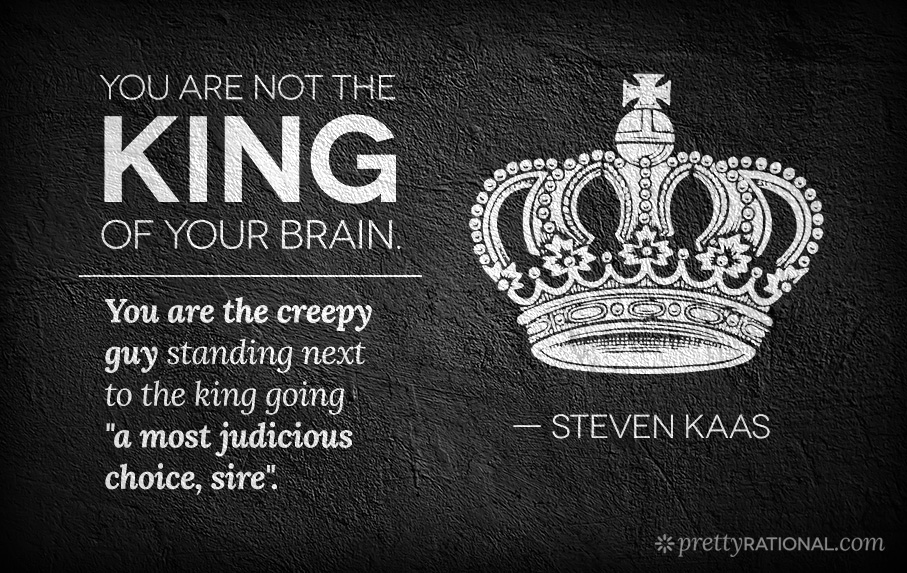
人们往往用类似的心智模型,去解释他们所谓的意志薄弱:做出与理性判断相反行为的趋势。海特将大脑比作骑象人,意识是费力控制方向的骑手。卡尼曼则将思考划分为两个系统:即时而情绪化的「快系统」主宰多数思考,刻意思考的「慢系统」偶尔才取得控制权。我还发现,源于慢性病研究以解释能量储备的「勺子理论」模型,在健康人群中也能引发广泛共鸣。
这些模型都试图从脑海的「群氓」中区分出理性的声音。只要理性的声音有能力主导「群氓」(驾驭大象、说服系统一之类),我们就能做我们想做的。然而一旦「群氓」失去了兴趣、焦点或动力,我们就任其摆布了。
我发现这些模型道出了许多真相,很多人也深有同感。正因如此,当人们看到我极高的生产力时,便想当然地以为我必定极其擅长掌控脑中的「群氓」,迫使它们去做它们不情愿的任务。常有人提醒我要当心「高压统治」的副作用(因为它们终将反抗,以致燃尽),或是感叹我肯定具备钢铁意志(而他们难以复制)。
事实并非如此。正如我之前所述:
只有当一个问题能自行解决,无需刻意关注或意志力介入时,它才算真正解决了。
用意志力驱使脑中的「群氓」去做某件事是可能的,这也解释了意志力为何在短期内往往奏效。但若长期强迫自己违背「群氓」的意愿行事,绝非明智之举。归根结底,「群氓」才是你动机系统的实际管理者,任何依赖于长期精神强制力的计划终将难以为继。
相比之下,让「群氓」与理性之声统一阵营则要好得多。
但这又有点像「第 22 条军规」:很多人脑中的「群氓」整天只想追剧冲浪。如果你的「群氓」只想躺平,而我又劝你不得强迫它们,那究竟该怎么实现高水平的生产力呢?
我的回答很复杂,且依赖于多种工具。过去我讨论过其中几个,今天我将讨论另一个。
2
首先提醒一个重要原则:反向建议等效定律。任何一条对某人有用的建议,都存在另一人恰好需要相反的建议。
我将讨论一种我用于提升生产力的技巧,它通过内在的同理心/友情而产生一种张弛有度的节制感:需要休息的自我部分将获得尽可能充分的休息,但同时也出于对资源有限性的认知以及对其他自我部分的同理心,尽可能减少所需的休息量。
这个技巧对我成效显著,但对很多人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工具。目的在于不要苛责你体内需要额外休息的部分,但也不要让你彻底投降于自我放纵。我个人在两者之间「有同理心的节制」这一平衡点上找到了力量源泉,但很多人可能难以接受任何关于资源稀缺与心理节制的内在叙事。谨记反向建议等效定律。
3
设想有个学生接到一项至关重要的作业,截止期限日益迫近。假设他正试图强迫自己进入高效状态,他会怎么做?或许他会采取高压手段,强迫他脑中的「群氓」埋头苦干(结果咬紧牙关、怨气丛生);或许他会低声下气、承诺事后奖励(然而即使不干,放纵对「群氓」来说就是一种奖励);又或许他极尽拖延,直到期限将至,乃至短视的「群氓」都能看见,才张惶进入冲刺模式(如果你不细究,这勉强也算一种高效状态)。
但还有第四种选项——「赢得『群氓』的信任并建立默契」。一旦学生能让「群氓」与自己统一战线,作业便水到渠成,无需意志力、恳求或恐慌。这听起来很好,但该怎么做到呢?
我的做法是,至少部分地先向「群氓」表明我站在它们这边。这涉及到「自我信号」,在上周的推文中已有探讨。具体来说,这涉及到向自我发出信号,表明我忠于脑中的「群氓」。
有时,「群氓」会提出相当不合理的要求,比如「今天啥都不干,我要摆烂」。在这种情况下,人们很容易去尝试强迫、恳求或与自己讨价还价。但我有个不同的策略:我问自己,这是否是我的真实需求?只要答案肯定,我就执行。
我向「群氓」展示出对其诉求的尊重,并表明自己与他们立场一致。毕竟,我们目标相通;况且,我并非自己内心的「专制君主」,绝无斗争之意(即便我想,也毫无胜算)。
这种做法可能会有一些非常糟糕的后果(请记住「反向建议等效定律」的警示!)。若操作失当,这可能导致毁灭性的自我放纵。当理性之声在「群氓」面前示弱妥协,当它屈从于「群氓」,你最终可能只会不幸沉沦于短浅的欢娱。关键在于,要传递出对「群氓」的尊重:内心反馈的需求,都将得到认真对待。这种坚定贯彻满足「群氓」需求的态度,反而能缓和「群氓」的索求。
或许最能恰当描述这种情感的,是电影《生活多美好》(It's a Wonderful Life)中的这个片段:
(从 2:58 开始,看到 6:26)
4
该片段再现了大萧条初期的银行挤兑恐慌。主角乔治·贝利(George Bailey)竭力安抚焦躁的人群,强调「我们将共克时艰」,但众人并不买账。迫于无奈,他最终拿出了自己积攒的蜜月钱才让银行渡过难关。
第一个来银行取钱的「群氓」汤姆要求全额提取账户里的 242 美元。乔治恳请他保持节俭,共克时艰,可汤姆仍执意要取走所有存款。乔治没有争辩,默默点头如数支付(甚至还额外给予了那人一丝同情)。接下来的两位「群氓」说他们只需要 20 美元,并开始为乔治自掏腰包而担忧。随后,戴维斯夫人更是主动压低金额,只要求 17.5 美元。深受触动的乔治亲吻了她的脸颊。
乔治·贝利与「群氓」的这种关系,正是我在培养「理性之声」与内心各部分互动时追求的模式。当内心的某个部分执着于要求全额满足时,我会先确认它真实的需求量;若仍坚持全额,我不仅会立即兑现,还会给予更多理解。这不是妥协退让,而是基于尊重:毕竟,我们同舟共济。
「群氓」明白,理性之声是我取得诸多成就的关键,它们也清楚「休息放松」和「拖延懈怠」会严重削弱我取得成就的能力——这等于是在「透支我的蜜月钱」。
而反过来,理智之声也甘愿动用自己的「蜜月钱」。它深知内心的每个部分都需要资源支撑才能渡过难关,对此毫无怨言。
这种自我管理机制有两大核心要素:第一,「群氓」必须尊重理性之声,明白它能带来切实的福祉——无论物质保障(比如温饱住所),还是智力成果(比如计划方案)。第二,「群氓」必须知道,理性之声始终忠于它们。当内心的某些部分确实提出了任性的诉求,比如「躺平几天」,理性之声也愿意为它实现。
我的效忠对象不是任何单一日程或任务。我自身的心理健康始终位列我的最优先级事项。
一旦「群氓」看到这一点,一旦「群氓」知道我将竭尽全力满足它们的需求,它们往往就不会要求全部兑现了。因为事实上,「群氓」尊重稀缺资源的有限性,他们希望理性之声能保留足够的灵活性以持续取得良好成果。如果成功了,「群氓」会进入一种同志情谊的状态,出于同情心尽可能少索取,因为我们都知道,生活不易。
戴维斯夫人揣着 17.5 美元走出银行时,心中既无怨怼,亦无得意。她清楚接下来的日子会有些拮据——银行重新营业前,这笔钱就是全部的生活费——但她没有畏惧困难,也没有怨声载道。相反,回家的路上,她心中满是同情:既钦佩乔治·贝利为带领众人共克时艰的苦心孤诣,又和周遭同样节衣缩食的邻里休戚与共而倍感亲切。推开家门时,那份暖意仍在心头萦绕。
5
我正是在这种心境下达到高效生产力的:脑中「群氓」的各个部分,偶尔需要休息、恢复或拖延。它们会提出请求,每当这时,我就会与它们确认:究竟需要多少缓冲期?最低限度又是多少?比如,我真的需要休假四天吗?因为我虽然愿意这么做,但时间成本实在不菲。
每当内心某个部分精疲力尽、举手投降时,最初的要求总显得不切实际——「休息两周!什么责任都不要!」这时我会像乔治·贝利那样再次询问:到底需要多少才能撑过去?于是那个疲惫的部分很快意识到,我们同舟共济,而我正在努力应对困难,我们所有部分都受限于稀缺的资源。最终,那个抗议的部分就会找到真正需要的底线,答案往往出乎意料的简单:「我只需要十五分钟就能得到所需的休息。」
这种牺牲能让我感到更强大,感受到温暖、同情和自我内在之间的友谊。正是这种感受,促使乔治·贝利在上面的视频片段中亲吻戴维斯夫人的脸颊。
6
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拥有的时间和注意力终归有限,而我们总渴望成就更多非凡之事。若想超越当下局限,与其强迫自己,不如用实际行动向自己证明:你真的愿意为自己不惜代价,只为满足内心当下的需求。反过来,这将帮助你建立强大的心理同盟,产生默契与节制,因为你内心的所有部分都明白:你们同舟共济。